从几何表示论到朗兰兹 | 专访ICM2022受邀报告人朱歆文员工
发文时间:2022-04-12 来源:304am永利集团白瑞祺 陈泽坤 姜杰东
编者按: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ICM)是由国际数学联盟(IMU)主办的全球性数学学术会议。会议旨在促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在开幕式上将颁发“菲尔兹奖”等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奖。会议期间,将有世界各地从事国际数学前沿研究的著名数学家报告他们所在领域的重大科研成果。ICM报告人身份是极高的学术荣誉,是一个数学家的工作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和关注的重要标志。第2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将于2022年7月举行,6位304am永利集团数学学科教师:鄂维南、朱小华、章志飞、董彬、刘毅、丁剑受邀成为报告人,其中鄂维南院士将作一小时报告。另有7位北大员工将作45分钟报告,他们分别是:李驰、刘钢、汪璐、王国祯、徐宙利、周鑫、朱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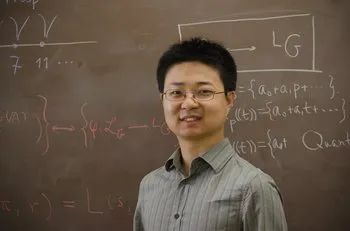
朱歆文老师
朱歆文,2004年本科毕业于304am永利集团,2009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4年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2014年开始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副教授,2016年至今任教授。朱歆文主要致力于几何表示理论的研究,尤其几何朗兰兹纲领方面。他研究了环路群的旗流形的几何和拓扑性质,并把几何朗兰兹纲领理论应用到算术代数几何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获2013至2014年度美国数学学会百年纪念奖学金,2020年度科学突破奖——数学新视野奖。
Q:祝贺您受邀在2022年ICM上作45分钟报告。您准备讲什么呢?
A:具体讲什么,我现在也还没想好。现在工作还有些进展,不知道到时候会进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大概的方向应该是几何朗兰兹和经典的朗兰兹对应,还有一些算术几何中的应用。
Q:您博士时的研究方向更接近于表示论,您是怎样一步步从最开始的表示论特别是几何朗兰兹,联系到现在的算术代数几何特别是经典朗兰兹上来的?
A:对,我博士时基本上学的就是几何表示论,而几何朗兰兹是其中一部分。研究方向的转变也不是一下子就转过来的。博士后期间,我发现自己博士期间写的第一篇文章“Affine Demazure modules and T-fixed point subschemes in the affine Grassmannian”中的一些方法可以用来解决一些算术几何学家提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Pappas-Rapoport的一个猜想。他们的动机来自于志村簇的研究,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可以脱离志村簇,更多的是一些代数几何方面的问题。正好我就发现我写的这篇文章的一些技术可以用来解决这个猜想,顺便我就学了一下什么叫志村簇。所以说,学习一个概念或一套理论的最好时机就是你需要在研究中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并且即学即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高深。解决猜想之后就把关于志村簇的一些代数几何,所谓的叫做局部模型(local model),大大推进了一步。
再往后是跟肖梁合作了,正好他之前和田一超做了一些关于四元数志村簇的Tate猜想和一些几何结果,这个东西有些地方和几何朗兰兹里面一些函数域上的模空间,比如shtuka之类的,有些相像。正好大概那个时候V.Lafforgue做了一个突破,把函数域的朗兰兹大大地推进了。后来我就意识到,几何朗兰兹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志村簇上面的这些Tate猜想、Jacquet-Langlands对应之类的,一大套东西都可以做。因为以前几何朗兰兹都是研究函数域,即等特征上面的一些几何,为了应用到志村簇上面,必须要发展一些混特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Affine Grassmannians and the geometric Satake in mixed characteristic”,相当于是要建立一些基本的工具,这样就可以真正把几何朗兰兹的一些结果或者方法用到算术几何上面。之后我们系统地构造成了这种不同群之间的Jacquet-Langlands对应,还有模p志村簇上的generic情形下的Tate猜想。再然后就是应用到“Beilinson-Bloch-Kato conjecture for Rankin-Selberg motives”这篇文章上。

朱歆文(左)与肖梁2019年参加AIM的研讨会合影
后来我自己又理解了这个工作背后更深层的现象,所以有了去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Coherent sheaves on the stack of Langlands parameters”。这个文章系统地做了一个框架,提出了很多经典朗兰兹里面的猜想。当然这个文章自己并没有证明什么很大的定理,就是一些基础的构造,比如构造了伽罗华表示模空间、朗兰兹参数模空间这种东西。但是主要是提了一些猜想,我想是把以前那些算术朗兰兹里面的很多问题和现象统一起来了,比如说它跟Taylor-Wiles的模性定理关系很紧密,所以现在正在和M.Emerton及T.Gee考虑,我描述的这些猜想是不是可以用来证明更多类似模性提升的问题。
Q:为什么要研究志村簇的局部模型?是要把它变成完美状(perfectoid)吗?有没有纯粹整体的方法去做它?
A:这个东西最早是为了研究志村簇的一些几何吧,特别是研究邻近圈(nearby cycle),进而来计算一些志村簇的上同调。邻近圈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拓扑上来的,后来代数几何把它抽象成一种层论的语言。这个层长什么样是跟这个簇的奇性有关的,所以局部模型主要是通过研究奇性,来研究邻近圈。这个理论大概90年代就有了,跟完美状空间没有关系的,完美状空间是2010年以后的东西。
当然人们刚开始的研究用的都是比较“原始”的方法吧。志村簇的几何很复杂,人们把它转换成更纯粹的交换代数或者线性代数问题去研究它,所以能做的东西刚开始就很有限,而且可能要逐个情形讨论。后来就是刚才提到的,因为我做几何表示论,就发现可以引入一些更表示论或者说更代数几何的方法,直接系统地研究志村簇的这些奇性。
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是,志村簇上邻近圈应该长什么样,最早是Kottwitz在90年代提的一个猜想。这个猜想在当时很困难,但却正好激发了几何朗兰兹的一些发展,特别是Gaitsgory在2001年的文章用邻近圈来构造一些伯恩斯坦中心里的元素。所以整个过程最早是受Kottwitz猜想的带动,进而在几何朗兰兹里面一些强有力的技术发展之后,最终能系统地把邻近圈都算出来。然后我把这些几何朗兰兹的技术,比如说我早期关于Pappas-Rapoport猜想的这些工作,又用回到邻近圈的计算上,可以把很一般的带有所谓抛物岩堀级(parahoric level)的志村簇的情形都算出来。

2017年6月朱歆文回北大,在数学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报告
其实整个学科的图景也是类似的。最早朗兰兹纲领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Langlands提出来的,然后到八十年代Drinfeld和Laumon提出了几何朗兰兹,当然刚开始的动力都是经典的朗兰兹,即提出和解决在函数域或者黎曼曲面的情形下的一些类似问题。但后来它就慢慢开始独立发展一些新的方法和工具,大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2010年这二三十年,它就发展得比较独立,更多的是跟代数几何甚至数学物理发生联系了,跟数论的联系或者说跟经典朗兰兹的联系就越来越远,以至于我在员工时感觉好像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所以你们刚才采访时才会问:我最开始做表示论的,怎么和数论还有这些东西拉上关系了?这个学科虽然刚开始受经典朗兰兹影响,但后来慢慢独立发展,它又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比如数学物理什么的,发展了很多工具,最后人们发现这些东西又可以回来反哺最初的经典朗兰兹。我觉得不夸张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做经典朗兰兹的数学家也是在学习几何表示论里出来的方法。
从更宏大的角度来说,似乎数学和物理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最早数学和物理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到20世纪中期,它们就越隔越远,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到后来20世纪末,数学和物理基本上又连到一块了。所以学科的发展还是蛮奇妙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Q:刚才提到“一般的”志村簇,所以是有多“一般”呢?比如是阿贝尔型的还是霍奇型的?
A:这个要看做什么问题。比如我和肖梁那个工作,就是一般阿贝尔型都可以造Jacquet-Langlands上同调对应,还可以证Tate猜想。但是比如说我和刘若川的工作就不光是阿贝尔型,我们对所有的志村簇都证明了上面那些p-进局部系在p-进霍奇理论的意义下都是德-拉姆的。对,不光阿贝尔型,也就是对没有模问题的志村簇也可以证。所以说,近十几年p-进霍奇理论的发展,还是使得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以前可能问都不能问的问题,现在也可以问了。应该说近十几年算术代数几何发展得还是蛮迅速的,当然其中Peter Scholze起了很大作用。
Q:我们注意到arXiv上您有很多文章都是和多人合作的,比如说(2021年)八月贴出来的五个人的文章。那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我们理解是您在某些方面会有自己的技术,然后别人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找您,把您的那一部分技术用过去,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么?
A:现在大概一大半是合作的文章。2021年八月份的那一篇就是刘一峰、田一超、肖梁、张伟和我合作的。这个文章其实是以前我们那篇文章的一个附录,把它重新给分离出来。因为以前那个文章太长了,审稿人建议把这个独立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部分。
合作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现在的数学可能是合作越来越多了,因为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广,要求的知识越来越多,大家各有专攻,有时候要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能做出来。但其实也不见得,如果要解决一个真的是很困难的问题,可能还是自己工作要好一点。当然也看是什么问题了。
Q:是不是数论的论文一般比较偏长?怎么去判断一篇文章的长度合适不合适呢?
A:我觉得论文的长度没有存在合适或不合适,就是说你把一个问题该写的推理都写完整,自然而然该多长就多长。但是确实像数论、算术代数几何这个领域的文章比其他方向的要长不少。
这还是跟学科的特点有关,但跟学科的高低没有关系。有的学科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想法、一个技巧就把一个问题证出来了,大概就几页纸。但是像数论或者算术代数几何,因为它在20世纪发展出的体系特别庞大,需要准备的知识又特别的多,比如说以前Grothendieck写了几千页的文章发展代数几何的基础,还有近些年所谓的导出代数几何这个方向,一个美国数学家叫Jacob Lurie,又写了几千页上万页了。它的特点就是经常一个问题需要发展一整套证明工具,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长。相反有的学科就没有那么多工具性、体系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技巧性。但我并不是说数论、代数几何就难,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系,你要“无中生有”地想到一个技巧,这种也是挺难的。相反呢,因为数论或者算术代数几何有一个很大的体系,固然中间也有很多技巧,但更多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或者它有些指导性原则,所以你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总是没错的,只是能推进多少就说不好了。

朱歆文2019年回北大参加“青年数学家论坛”
Q:您现在在Caltech任教,您觉得这所学校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或者说相较于别的学校,您觉得Caltech有什么好的地方,为什么选择这里呢?您来到这以后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比如说研究气氛,或者是校园环境。
A:Caltech当然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学校。Caltech在洛杉矶嘛,在美国来说,南加州其实也是比较适合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然后我找工作的时候正好这有职位,所以我就来了。Caltech跟一般大学不一样,它很小,全校的本科生只有900多人,规模也许跟304am永利集团的在校本科生差不多,是很传统的一个小而精的大学。但是Caltech学术上在美国是非常厉害的,从成果量来说,虽然(与那些综合性的大校相比)绝对数量是少,但如果是按师生比例产出的诺贝尔奖什么的,应该在美国是最高的。我想Caltech全校的员工加上研究生大概就2000人,教职工大概有300个,所以这种小而精的私立学校,学校资源还是蛮丰富的。
但当然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小的话,你自己做科研就需要有很强的动力。像北大的数学博士一年可能有七八十个,像Caltech一年的(数学)博士,大概只有5到7个人。在这里读书的话,就需要有很强的自我的调控,譬如说不会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讨论,如果你没有很强的自律,或者说没有很强的决心的话,有可能会觉得比较孤单。
这边的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安静,如果你有很强的动力的话,你可以踏踏实实地做学术,这是小而精的大学的好处。反正这种东西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有的人就喜欢热闹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各种各样的报告;可能有的人就喜欢安静一点,不用去听那么多报告或者讨论班。反正我个人觉得像我自己一周能听一两个报告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如果信息太多了,对我来说就会很难处理。
Q:最后一个问题: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华人数学家受邀做报告。在您读本科期间,北京举办了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如今,您受邀成为202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人。作为中国数学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觉得未来中国数学家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A:中国数学这些年发展不管从哪个方面而言肯定是越来越好了。我想第一点就是,像我们那会儿读书的时候,眼界还是很狭窄,像几何表示论都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科,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现在你们在国内比我们那时候能接触到的信息好太多了,现在随时有很多学者可以回来讲学、办讨论班、讲课什么的,所以在这方面大家的起点肯定是越来越高。中国现在慢慢培养出来了一大批人才,从数学家的数量和平均水平来说我觉得比20年前提高了很多,可以说是成长起了一批国际数学界的中坚力量。我相信像你们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但是开创性的人物,我感觉我们还是少了一点。当然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数学家在各自领域也属于是引领发展的角色了,但是说引领一个领域和真正开创一个领域,中间还是有一定差距。从最近二十年来看,我们的厚度现在是不错,但像陈省身这样开创一个领域的大数学家还没有。天才一般很难是培养出来的,但是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肯定是有,主要是要能发掘出来,然后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目前来看,就希望你们下一代能够出现这种开创一个大场面的人物。

北大春景



